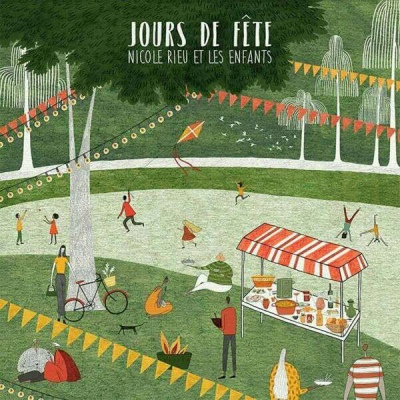天九娱乐太武帝滅北涼後,命崔浩監秘書事,主持監修《國紀》,而高允與張偉領著作郎去編寫。當時崔浩寵信著作令史閔湛,閔湛不但上疏稱許崔浩所注釋的《詩經》、《論語》、《尚書》及《周易》更勝馬融、鄭玄、王肅及賈逵所注釋的經典,建議都收集全國所有前人注釋經典的書,而改用崔浩注釋的版本;又求下詔命崔浩注釋《禮記》,以讓天下人得知《禮記》的正確解釋。及後更勸崔浩將寫好的國史刻在石上,想用這種能長久保存的方式彰顯崔浩直筆寫史的事。崔浩和皇太子拓跋晃都同意這樣做,最終在平城西郊祭天壇東三里建成了刊載《國記》及崔浩所注《五經》的大型石銘林。高允得聞此事後,就和諸作郎宗欽說:「閔湛所做的,短時間內恐怕造成崔家極大的災禍,連我們也不剩了。」這些石碑都放在道路旁當眼處,看過的行人都對其直書北魏一些史事有所不滿,並很快就讓太武帝知道,終令崔浩和其家族清河崔氏被族誅,並因而波及其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及河東柳氏。而崔浩被收捕那晚,高允正在中書省當值,皇太子拓跋晃特別命東宮侍郎吳延召見高允,並讓他留宿東宮。明天一早,太子命高允隨行去見太武帝,表示進去後自己會在太武帝面前為他說話,並囑咐即使太武帝有問題要召他也要和自己說的口徑一致。進去後太子即向太武帝表示高允在東宮做事多年一直小心慎密,得自己信賴,修國史一事雖然和崔浩共事,但一直是受制於崔浩,求獲特赦。太武帝及後召高允進見並問他國史是否都是崔浩寫的,但高允卻如實答:「《先祖記》是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是臣和崔浩一同寫的。不過因為崔浩事務太多,他只是從總體作裁定而已。至於注疏方面,臣比崔浩參與更多。」太武帝聽後大怒:「這樣比崔浩更重罪,哪裹還有活著的理由!」太子隨即嘗試為高允開脫:「皇帝的威嚴太強了,高允只是小臣,所以迷惑錯亂,表現失常。臣之前問過他,他是答崔浩寫的。」太武帝再問高允是否如太子所言,高允又直說:「臣以低下的才能,錯誤地參與了著作國書,觸犯了皇帝的威嚴,罪行應予滅族,今天已經是死定了,不敢作假。太子殿下因為臣長期為他侍講,所以想留住臣的性命罷了。他根本沒問過臣,臣也沒說過這話。臣據實回答,並沒有迷惑錯亂。」太武帝見狀就向太子說高允明知要死仍不堅定不移的行為是相當難得,而且堅持對君主說實話是忠貞臣子,決定饒過他。及後太武帝大怒之下命令高允寫詔書,要上至崔浩,下至其僮吏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部都夷五族。高允卻一直拖延,在一直催促下他請求朝見太武帝後才寫,但朝見時卻說:「因崔浩而連坐的人,臣不知他們是否還有別的罪,但若只因此事,罪不致死。」太武帝聞言大怒,命武士將高允抓住。太子聞訊又去為高允求情,但太武帝也因高允的話而改為只族滅崔浩,其他人就只誅其本人。事後,太子責問高允為何不聽他的話,就是要觸怒太武帝。高允就表示史書是帝王的真實記錄,亦是後世明顯的警戒,故此要詳細記載君王的事跡以讓後來者所知,故此在國史之獄上其實是崔浩因自己愛恨私慾而有負聖恩,致遭滅族,但在史籍上書寫帝王起居事跡和記載朝廷得失本來就是寫史的原則,沒有甚麼問題;又說自己和崔浩一起寫國史,生死榮辱就當連在一起,不應該有所分別,故此得到赦免是出了他自己的意料。太子聽後動容感歎。
“邯郸”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谷梁传》,史载:“襄公二十七年:故出奔晋,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但是并未说出邯郸地名的由来,一般流行的说法是颜师古《汉书》注解中引用张晏的解释:“'''邯'''”字来自山名,即古时的邯山;“'''单'''”是山脉尽头的意思,因作城郭名,所以加“邑”(阝耳朵旁)为“'''郸'''”。大概意思是,邯山到此而尽,故名邯郸。而《后汉书·光武纪》注解也是这样:“邯,山名。郸,尽也。邯山至此而尽。城郭字皆从邑,因以名焉。”古称'''邯'''
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南北,把秘鲁分为三个地理区:山脉以西的沿岸区是狭长的平原,除季节性河流河谷地区外气候干旱;高原区即安第斯山区,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和全国最高的山峰──海拔6,768米的瓦斯卡兰山都位于该区;第三个区域是佔全国土地面积60%的亚马孙林区,区内是被亚马孙雨林覆盖的广阔的低地,位于山脉以东。
 免费下载
免费下载